
《天津日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纪念专刊计生工作三十年
全文转载
吴凤兰:“天下第一难”干了一辈子(图)

吴凤兰,一位在计划生育战线上摸爬滚打了30年的老兵。听她讲计生故事,就像是找到了一条线索,串起了计生工作30年的发展变迁。
谈起计划生育,人们就会想起上世纪90年代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在它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史的奇迹,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有效控制两大难题后的今天,计生工作已不是人们眼中“只管生一个”的简单概念,从关注育龄妇女开始走向关注生命周期的全过程。
过去,我们主要为育龄妇女服务。现在,从0岁开始的优生优育到空巢老人,从青春期生理健康到生殖健康,从流动人口到困难群众,通俗地讲,从生到死,都成了计生工作研究的课题。
“1979年2月14日,我被调到河北区王串场街计生办。”30年过去了,吴凤兰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日子。“因为那天在铁路俱乐部开大会,讲人口剧增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倡导‘只生一个好’,动员人们领独生子女证。当时,够4岁间隔的可以领生育指标。比如1975年生了一个小孩的,那么1979年就可以领生育指标再生一个。我的任务就是动员已生小孩的家庭退生育指标。那时,我才24岁,还没成家。给育龄妇女做登记时,像避孕措施那些问题我都不懂,也不好意思问,为这没少挨领导批评。当时人们还是很封建的,婚育知识少。我记得那时最难做的工作是老人,因为大多数年轻人都听单位的同意生一个,关键是家里老人不同意。我们常常上门跟老人谈心,讲‘算账对比法’——如果两个人养一个孩子生活就富裕,孩子营养好,大人也有时间精力照顾教育;若一个人养三个孩子,生活困难,费心费力也照顾不好。当时的任务还不算重,只要有10%的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就达标。后来,独生子女率才从10%提高到30%再到50%。”
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写入了宪法,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也就更加严格。吴凤兰说:“计生工作被认为是‘天下第一难’,难就难在我们要时时刻刻挨家挨户地走访、了解、动员。为了准确地控制人口,每年要做好人口计划。比如说,今年的指标是允许生400个孩子,眼看指标要超了,我们就赶紧给育龄妇女做工作,建议她3月份以前不要怀孕,等4月份以后再怀孕,这就算隔年的指标。现在我们基层不需要做人口计划了,什么时候怀孕都可以,很人性化。过去做计划是因为人口增长太快,不得已而为之。1982年我调到粮店街计生办,那是一个有2万人口的街,一年生300到400个孩子。现在,我在江都路街,有近5万人口,每年才生200个孩子。”
90年代,我国人口开始走入平稳增长阶段,从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转化。计生工作也从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工作方式也由单纯依靠行政手段逐渐向以人为本、优质服务、综合施治转变。吴凤兰说:“90年代,很多‘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单纯靠行政命令已经行不通了。刚开始,我们也不适应,尤其是如何解决下岗女职工超生的问题。你如果生硬地讲政策,人家肯定不听。为了取得人家的信任,我们做得最多的就是自己找关系搭人情为她们找工作。”
2000年,时代赋予计生工作更丰富的内涵,它再也不是人们眼中“只管生一个”的简单概念了。吴凤兰说:“过去,我们主要为育龄妇女服务。现在,从0岁开始的优生优育到空巢老人,从青春期生理健康到生殖健康,从流动人口到困难群众,通俗地讲,从生到死,都成了计生工作研究的课题。2000年,我调到了江都路街。我们分析不同的社区文化,因地制宜地开展计生工作。比如说通达新苑社区,是年轻的文化型小区,我们就找独生子女成才的典型,给大家介绍经验。乐山里是80年代的铁路宿舍,老年人多,我们就搞居家养老服务。过去,我们不受欢迎,现在是大家需要我们。举个例子,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我们就把查孕扩展为查体,今年参加查体的有2800多人。因为确实有很多人查出了大病,得到了及时救治。有一位40多岁的下岗妇女,查出有子宫肌瘤,但她坚持说自己没病,只是肚子胖。我了解后发现,她下岗后一直领失业救济金,爱人70多岁,孩子上初中,家里生活困难。我马上与医院和劳服联系,为她摘除了一个6斤多的肌瘤,并报销了医疗费。”吴凤兰说:“过去,天津外来人口并不多,遇到‘超生游击队’那样的情况,我们就是让他们离开。现在,天津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我所在的江都路街,有很多外地人在这卖菜,但他们住在东丽区,这就形成了管理的盲区。为此,我们常常去他们卖菜的市场转悠,看到小孩子,就询问月龄、做登记、提醒打疫苗的时间,生怕漏下一个。”
吴凤兰快退休了,但这份让她干了一辈子的计生工作越干挑战越大。人口问题,是关系到家家户户幸福的大事,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未来的大课题,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的主题。30年的思考还在继续,30年的努力还在继续,30年的探索还在继续……(本报记者 韩晓晶 摄影 刘耀辉)
中国国情下的计划生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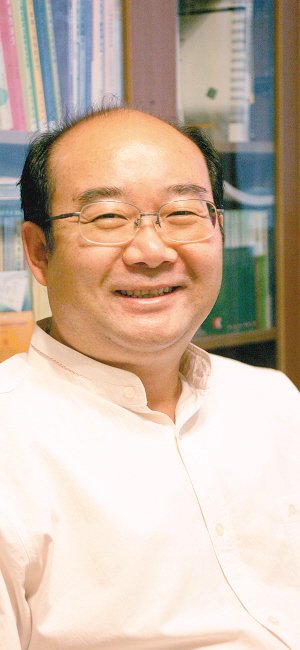
原新,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科学地讲,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动态的、多元的政策。如果没有当初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对人口数量进行有效的控制,难以想象今天会是一个什么状态。生育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是好的状态。我们可以分区域进行研究,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道路。
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50年代中到60年代中,10年间人口净增加1亿人。紧随其后的10年人口净增加2亿,在70年代中达到9亿人。由于快速的人口增长,我国从60年代就开始在京津沪一些大城市开始推行计划生育理念。7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倡导计划生育政策,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量,迅速从1971年的5.8个减少到70年代末期的2.4个孩子。尽管如此,因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口总量依然保持平均每7年净增加1亿人。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著名的“925公开信”, 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党团员要起带头作用。这就是所谓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谈到“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与计算机还有一段不解之缘。70年代中后期,从国外引进的计算机是个稀有物件。当时的一些著名科学家,通过计算机模拟了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过程,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平均每对夫妇只生育1个孩子,那么到2000年,中国人口就可以被控制在12亿以内。这项研究成果被演化成为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事实上,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来没有覆盖100%的人群,少数民族和边远山区就从来没有实行这个政策。客观上,实行严格的“一胎”生育政策,仅是指从1980年9月到1984年4月。因为实行后发现,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矛盾。首先,农村的包产到户必然要放大孩子的经济功能、劳动力功能。第二,那时农村没有养老保障体系,只有一个女孩的家庭,父母40岁时就是空巢家庭了,那么谁来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于是1984年4月,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了调整,在一些地区农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子,可以再生一个,简称“一胎半”政策。科学的讲,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动态的、多元的政策。
从1992年开始,我国开始进入低生育水平,至今已经17年了。期间逐步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第一,人口结构老龄化。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达1.6亿人,占总人口的12%。第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120个男孩比100个女孩,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第三,人口年龄结构呈枣核型,两端为低龄和老龄,中间为中青年,劳动力资源供给丰富,因此造成就业压力大。此外,出生人口素质、人口流动迁移、人口合理分布等问题也日益显现。2006年,中央提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计生工作的服务范围从育龄妇女转向生命周期的全过程。
目前,学术界对计划生育政策有一些讨论。我认为,任何政策都要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去看。如果没有当初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对人口数量进行有效的控制,难以想象今天会是一个什么状态。任何政策也要与时俱进。生育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是好的状态。我们可以分区域进行研究,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道路。(本报记者韩晓晶)
松慧热线:倾听孩子们的心声

黄松慧,天津市河东区唐家口街道久福园社区计生主任。由于参加了中美合作开展的青春期教育培训项目,身为母亲的松慧忽然明白,原来孩子的任性是青春期惹的祸,如果把这个蕴藏着无数秘密和知识的宝库,与孩子们一起分享,该有多好。于是,一个专为青少年朋友服务的“松慧姐姐热线”诞生了。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已经成长了几代的独生子女。他们的心理特点和成长问题,不仅关系到家庭幸福、学校教育、社会发展,甚至影响中国的未来。关注独生子女教育,关注独生子女青春期心理生理健康,是时代催生的课题,也是计生工作的服务重点。
在天津,有一个闻名的“松慧姐姐热线”,在3年时间里,这个热线接了2000多个来自不同地区的电话,有不计其数的孩子把不愿跟父母、老师、朋友说的话,都倾诉给了松慧姐姐,希望在她那里找到解开困惑的答案,甚至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黄松慧说:“孩子们的故事太多了,有一个特别典型。那是在2004年5月的一天中午,我接到一个电话,那是一个男孩,他声音急促地说他得了艾滋病,活着没有意思了,现在就想杀人,杀一个落一个,杀两个赚一个。我看他情绪激动就赶紧说,千万别这么做,我现在就去找你。他说,我在天津站,你不认识我,肯定找不到。我说,如果一个小时找不到你,你就实施你的行动计划。放下电话,我疯一样地骑车赶往天津站。站前人海茫茫,别说找一个陌生人,就是找个熟人都难上加难。我挨个问过路的人,‘看到一个十七八的男孩子吗?手里拿着小刀。’很多人以为我有精神病,都厌恶地躲开我。转眼离我们约定的时间还差十几分钟,我心里一下子空了,再找不到他,我就报警。那种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就像妈妈将要失去自己的孩子一样。当我走到十三路公交车站时,忽然一个男孩的身影闪了一下。透过穿梭的车辆和行人,看见他坐在路边,手里拿着小刀,目光呆滞。我的泪水哗地涌了下来。我说‘是你吗,宝贝?’原来他是当年高考的学生,查体时发现生殖器官感染,父母忙,没带他治疗,孩子以为自己得了艾滋病。我说带他去防疫站检测,他说那要求登记个人信息,不能去。后来,我们去了长征医院,我告诉医生,这是我的侄子,麻烦您仔细看看。医生说只是生殖器局部性感染。我们约定彼此保守秘密,他用高考的成绩来回报我。两个月过后,我接到这个孩子的电话,他考了598分,当年是高分,我高兴地哭了。”
黄松慧说,没有坏孩子,只是我们太缺乏教育孩子的常识和方法。有一位母亲曾找过我,她说她儿子总是背着她做事,母子关系越来越紧张。有一次,她看见儿子偷偷地写什么,刚想看儿子就把本锁抽屉里了。我劝她,孩子们想拥有小秘密很正常,等你不在意时,也许他会主动告诉你。7年过去了,那位母亲告诉我,在儿子的婚礼上,儿子说要讲一个小秘密,因为妈妈一直对我当年偷偷地写的那几行字耿耿于怀,其实我写的是“世上只有妈妈好”。
黄松慧说,也有一些情况令她困惑。“有个女孩给我打电话,让我带她做人工流产。因为这是第四次人工流产,医院要求家属签字。她不愿跟家里说,就找到了我。这个女孩的父母离异了,一直跟奶奶生活,常常遭周围亲属的白眼。她说没有什么值得在乎和惦念。我千方百计地找到她妈妈,但她妈妈拒绝和我交流,认为我多管闲事。像这样的女孩,多是家庭生活不幸福,家长不尽责任造成的,悔之晚矣。”
如今,当年打过咨询热线的孩子都已经成家有了孩子。黄松慧说:“前几天,一个年轻人来找我,他的外贸生意受经济危机影响破产了,欠了一大笔债。他要把自己刚满1岁的孩子托付给我,然后自杀。我一面劝他重新振作起来,一面正为孩子寻找助养。”
听孩子们的倾诉,黄松慧常常24小时开机待命。她说,孩子们常常半夜三更打电话。有时,手机烫得快没电了,又怕他们误会我不接电话,我就跑到离家门口最近的电话亭准备着。夏天,在外面一站就几个小时,两腿都咬满了红疙瘩。我爱人说,你疯了,再接电话就别回家。别人很难理解,其实获得孩子们的信任和期待,是最宝贵的人生财富。
这几年,不断有媒体出高价买黄松慧手中关于孩子们青春成长的案例,但都被她拒绝了。她说,尽管采用化名,我也不卖孩子们的隐私。每一个故事都是我的心血、我的眼泪、我的灵魂。我爱孩子,他们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我帮助孩子,但我不是神医包打天下。孩子的病都是心病,幸福的家庭不仅给自己一个好的人生,也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人生基础。
听松慧讲故事,仿佛心灵得到了一次净化,这是爱的力量。爱赋予我们生命,爱塑造一个个健康阳光的人生,这也是无数个工作在一线的计生工作者和志愿者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终点。(本报记者韩晓晶)
亲历者说
李敬之,一位73岁的老人,妇产科专家;王文祥,一位71岁的老人,农村小学教师。两位老人虽然身份不同,知识背景不同,但在那个崇尚多子多福的年代,他们却在感悟自己的生活场景中,主动选择了少生优生的幸福路,成为那个时代的先锋,那个时代的时尚。
天津在全国首倡“只生一个”
1978年12月3日,天津医学院44名教职员工起草了一份“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书。这是新中国第一份来自民间的计生倡议书。
在泛黄的倡议书签署人的名单里,第一列中有一个娟秀的名字——李敬之;第二列中有一个亲切的名字——李晓民,他就是李敬之的爱人。李敬之说,当时签倡议书的人,大都是30岁左右结的婚,而且不少同志只生了一个女孩。那时,我们的同龄人大都有三四个孩子。我和我爱人并不是党员,我们倡导只生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作太忙。那时候,如果不努力工作,真的就感觉对不起祖国。我上中学、上大学,都是国家出的助学金。我24岁从天津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总医院妇产科。我当时的领导是中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林巧稚的学生俞霭峰。她常跟我讲,不干事业的人没出息,必须当上主治医生才能结婚。结果,我29岁结婚。然后,领导又说,结婚两年以后再要孩子,不要影响工作。我32岁生的小孩。因为工作太忙,孩子72天就送了全托,根本没时间照顾。”
上世纪70年代没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妇产科病房里人挨人人挤人。床不够使,就把一张床加宽躺三个人,一个是刚生完的,一个是没生的,一个是准备生的。很多生了四五胎的妇女常常面临并发症、大出血等危险,对身体是极大的摧残。
面对“只生一个”这样超前的抉择,李敬之说,真的没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只是面对生活做出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
树桠多了花蕾少
我是受穷受累怕了
同样,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王文祥老人说,不是我思想有多进步,是受穷受累怕了。我母亲生了12个孩子,由于家境贫困只活了7个。我小时候,天天看见我母亲一夜夜在煤油灯下缝鞋。我父亲两头不见日头,天天在地里忙,累得30多岁头发没了、牙也没了。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上学受教育了。
我1963年结婚,1967年我有了两个男孩后,决定不再生了。那时讲究生“三男两女”,我妈说,没个女孩不齐全,你尽管生,我帮你照看。我说多生有什么好?我不能再走您的老路。因为孩子少,我在村里是富裕户。我有精力辅导孩子功课,我大儿子1982年考上大学,是大杨庄村“文革”后的第一个大学生。
采访时,王文祥老人被镇政府邀请,正为北辰区大张庄镇书写镇志。不知镇志中,是否也会记下他创作的诗歌“树桠多了花蕾少,苗儿密了长得弱,一对夫妻一个娃,育子成才人夸耀”。
大事年表
1955年3月1日 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报告,发出《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批示》,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国发出关于控制人口的政策指示。
1957年7月5日 《人民日报》刊登马寅初于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它系统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
1964年 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接近7亿。经国务院批准,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目标。
1965年8月 毛主席在接见卫生部负责人时说:“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国家计生委在天津召开计划生育座谈会,推广天津经验。
1975年 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发展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国家制定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的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
1982年9月 中共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1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1988年11月2日 天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1989年1月1日起施行。
2000年3月 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人口过多仍然是我国的首要问题,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以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2003年3月 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增加了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制定人口发展规划、促进生殖健康产业发展等职能。
2006年12月17日 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就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对于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全局,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